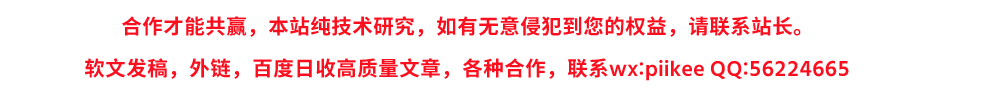遠字起名取名(起店鋪名字)
古詩詞常用來抒發情感,用于起名亦有黯然魂銷、心醉神迷的感覺。分享一些從唯美古詩詞取出的名字:遠思、時君、景林、青洲、晴明、如塵、長憶、佳期、青兮、和鶯、秋梧等,或悠遠,或唯美,或感嘆,或清雅。從古詩詞中取得的名字,都蘊含著詩人最真摯的情感,令人感觸、情難自已。
跟隨我的腳步,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今天分享這篇文章,給出生后還沒有名字的孩子選一個一生平安的名字吧。
這種咕嘟咕嘟的美食,大概沒有幾個人能抗拒吧!玉米餅,散養土雞、豆角、福建古田茶樹菇,多種食材放到一起,經過時間的燜煮,吃起來超美味。
「那會兒剛提的成績,感覺下半年最少能跑個210。」多年之后,張振龍對《人物》說。210指的是2小時10分。一條大路在他眼前展開,再下一站,就是奧運會了。他才20出頭,馬拉松運動員往往有更漫長的運動生涯,等待他的,也許還有更多的國際大賽。
瘋狂美發造型
何引麗還在大學時,殷長喜就幫她爭取烏蘭察布市體校的一份掛名教職,條件是她要代表那所學校比賽。徒弟的路,師父一步步都鋪好了。不止她如此。「他說只要是我招來的,我一定要對你負責,想辦法讓你考上大學,考不上大學也要給你找個地方去上學。」何引麗說。
剪草坊
2010年,一顆中國馬拉松新星在冉冉升起。4月大連國際馬拉松賽上,內蒙小伙兒張振龍跑出了2:13:28的成績。在那個時間段,全國能跑出這個成績的人不超過3個。那場比賽也是當年亞運會的預選賽之一,他將進入一個名單,在8月去北京集訓。
回復的第一句話很簡短:「最高級別那種。」
第二句話是:「差一步奧運會的馬拉松老將。」這與第一句話構成一個矛盾。
內蒙盛產馬拉松名將。胡剛軍在1997年以2:09:18打破全國紀錄,韓剛2007年跑出北馬歷年第二好成績2:08:56。歷年全運會馬拉松項目,內蒙隊七度奪冠。而內蒙古體育職業學院,就像鯊魚苗的養殖池,很多人才是在這里成長,進而被選拔進入省隊。
隊員間的第一道分水嶺是成為「二線」,這意味著你被劃為重點培養對象,但首先是實質的好處,吃飯有飯票了。當時隊里有70個人,二線名額只有18個。寒假到了,何引麗想加入隊里的集訓,教練說,「二線」免費,她留下來得自己花錢,她就沒留。那個漫長的寒假她完全未訓練,整整3個月,她在包頭的雪糕工廠里打工。
新教練的權威在第一天就建立了。比起前任教練,他罵人兇多了。「你們這群運動員,跟普通中學那些差太遠了,不認真。」何引麗有點怕他,很快她發現,所有人都怕他。
她能感到自己的進步。跟殷長喜練了半年,她躋身「二線」。2007年,她第一次跑馬拉松,就破3了。隨著中長跑成績穩步提升,她成為國家一級運動員,大學夢照進現實。依據周圍的有限信息,她相信自己是可以上北大的。北京體育大學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她還考慮過內蒙古師范大學,離家近,有體育專業。
她失去了大學校園生活,回報是成績的突飛猛進。2009年開年第一場比賽,她跑了2:37,下一場比賽,又跑出2:34。在她大學畢業的2012年,她在北馬跑進了230。這是一個里程碑的成就,代表著她進入到一個最拔尖的序列里。
但并非沒有快樂。快樂來自于贏,來自于領獎臺,來自終于登頂奧林匹斯山的那一刻。她記得勝利的感受第一次擊中她,那是一個房地產公司組織的小比賽,她跑了第三,掙了500元獎金,「高興了好幾天」。快樂只在終點存在,她不斷收攬獎牌。那種快樂讓她說服了自己,「我實質是喜歡跑步的,我從小就喜歡跑步」。
很多年后,張振龍仍然是一個殷長喜會對外人提起的名字。他是殷長喜旗下最早冒尖的隊員。他來自內蒙最北的呼倫貝爾草原,少年時,他在零下40度的雪地里穿著厚綿鞋跑步。他有著優雅舒展的跑姿。在2008年,他馬拉松能跑進215,別人還是一級運動員時,他屬健將級。
但在2016年的里約奧運選拔賽,她發揮欠佳,屈居第九。前三名去了里約。
跑了不到10公里,何引麗就感到腿腳乏力。她心亂如麻,中途就有了絕望感,想要退賽。倒是沿途跟車的殷長喜很平靜,「他說你隨意跑下來就好了。」沖過終點,她想,終于結束了。問題出在了賽前在青海的冬訓。殷長喜帶隊第一次上高原。他后來承認,高原和平原訓練方法不該一樣強度,賽前沒調整過來。殷家軍在選拔賽全軍覆沒。「有點練疲了。」隊員李春暉對我說。在向上匯報時,沒有歸咎他人,教練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
為了排解乏善可陳的生活,幾年前,她在宿舍里養了一條白色貴賓犬,訓練有時也帶上。這算是體校給她的一點特權,這是整個校園里唯一的寵物了。狗是她的軟肋。她沒給它做絕育,有次它發情跑去外面不見了,她動員隊友們在附近到處找,還貼了尋狗啟事。那是一些小隊員第一次看見「何姐哭了」。狗乖巧聰明,名字叫「米修」——英文miss you的音譯。她是孤獨的。
然后,疫情來了。2020年東京奧運推遲到2021年。
2020年的冬訓在海拔2000米的云南曲靖馬龍,這是何引麗第二次上高原。她想起4年前那次經歷,情緒上十分抗拒。出發前她和教練殷長喜講了幾次,「我說害怕,我不想上去,但是他說沒事兒。」她回憶,「他決定的事情不可能因為別人去改變,其實對我來說云南是硬著頭皮去的。」
在所有的線頭里,天才張振龍的消失是個謎團。在2022年秋,距離初次見面一年之后,我和張振龍通了一個電話。這是我們的第二次深談,上一次是因為另一篇報道,圍繞他的越野隊友梁晶展開。張振龍是認可那篇報道的,有了信任基礎,打開謎團的時機到了。
男生視角里展開的體校青春與女生是不同的,至少在早些年,校園暴力是觸手可及的現實,這是何引麗從未講述的部分。每個周末,摔跤隊那幫人喝完大酒,隨便踢開新生宿舍的門,不分青紅皂白挨個揍人,只有他們同鄉才能豁免。「我周六、周日從來都不在。」張振龍回憶,他躲去網吧包宿。李朋驗證了這個說法,他曾被六人圍攻,被鐵鍬斬開耳朵。
荒廢一年多,還是等胡榮教練調回地方,通過他的招募,張振龍才進入省隊。「如果要不是胡指導接的我,別人都接不了。」他聽到的說法是,殷長喜打了一圈電話,如果誰接手他,他不會輕饒那個人。但胡榮不同,他是殷長喜的師哥,帶過幾屆國家隊。但張振龍發現,他再也不是原來那個自己了。胡榮從不打人,但張振龍感到,新教練的體系無法適配他的體質,「練一段時間立馬就感覺出來了」。他的馬拉松水平只恢復到218,練了2年沒有起色,他早早退役。
輪到郭蒙緣上場比1500米了,她讓他制定目標,長著滿臉青春痘的男生卻撒起了嬌,「何姐」「何姐」地叫著。430吧,他說。不行,再快點,教練說。一番討價還價,定在425,郭蒙緣笑嘻嘻地離開了。后來,他告訴我,他其實最快能跑4分12秒,但前段時間做了手術,怕跑快了受傷。
文子、江姝、蕾敏、子義
圖|(除特殊標注外)視覺中國
- 熱門文章
- 最近發表
- 隨機文章
- 標簽列表
-
- 最新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