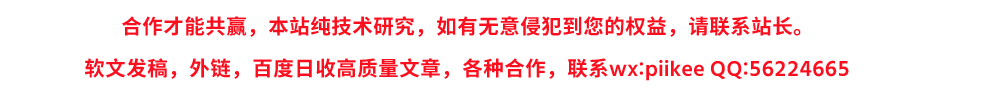天字起名字公司(天字開頭的游戲名字)
本篇文章給大家談談天字起名字公司,以及天字開頭的游戲名字的知識點,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詳情介紹:
奧美和得到換logo讓創意人方寸大亂
昨天,你們都知道的宇宙天字一號廣告公司奧美把自己用了70年的logo給換了。官方說,換logo主要是為了“溯源立新”,但是這個舉動不僅奧美內部的小散不開心,也在廣告圈炸了毛,刷屏的效果超過前兩天21家獨立創意公司結盟拒絕免費比稿。
新logo由前奧美人,現任美國天字一號的獨立廠牌廣告設計大師柯林斯操刀設計。這個事情其實蠻搞笑,因為偌大的奧美內部,在客戶面前指點江山的創意和設計大牛比牛毛還多,居然改個logo還要請外人動手,這到底是幾個意思?到底讓客戶怎么想?雖然說,藍標315在自己危機公關時被稱之為上了一堂“總監給自己理發”的公開課,并且那堂課上砸了,但是改logo這事,最多屬于化妝穿衣之類,總監還是可以自己做,而且應該自己做的。
好了,不說是誰做的也行,就logo本身,吐槽也是一邊倒,“不好看”“沒個性”“沒溫度”!一些人在朋友圈投票,某些公眾號也在底部放出投票測試,結果很多人還是覺得之前的logo好,說真的,那個拍板決定的人不怕大衛奧格威跳出來找他麻煩嗎?
向左滑查看更多評論
奧美上一次刷屏是在15個月前,同樣,那次刷屏并不是因為給客戶做出了驚天動地的案子,而是全球性的內部整合,推出所謂的“一個奧美”,并且在中國,尤其是在上海,把辦公室統統整合到火車站邊上的一棟樓里。
4A的衰落已經是大家懶得再討論的話題,但是,但是,能不能拜托奧美爭點氣,下次刷屏的時候是因為某個牛逼的案例,免得別人說“人丑怪事多”。
當然,換個丑logo刷屏這事,也不只是奧美會,中國最牛逼的說書人羅振宇一個星期前也玩過,而且玩得更666,因為他舉個人之力頂住了四面八方的各種壓力,硬生生地把一個丑八怪推到世人面前。下面這個就是羅胖力推的得到logo,你體會下。
羅振宇做得到,還有兩個聯合創始人,其中CEO脫不花當時說,如果用這個,我就不愿意來上班了。另外一個合伙人快刀青衣也表示當時就炸了,說最初的貓頭鷹還有一身毛,好不容易拼死相爭,把毛給拔了。
得到的內部設計師,不,很多同事分別為此開了很多小群,其中有設計師表示,如果最后選用這個,會考慮離職,因為怕影響以后的職業發展。
向左滑查看更多評論
但是,這個logo最終還是被采納了。
羅振宇的解釋是,一開始他也不喜歡,但是當聽到內部21個設計師都不喜歡的時候,他覺得這個設計的方向肯定是對了,因為,這個logo夠刺激,“刺激越大反應越大”。從獲取流量的角度,真的,他做到了。
別人家換logo,與你何干?logo好不好看,本身就是非常主觀的判斷。按理說,吃瓜的必要都沒有,但是為啥這兩次會在廣告圈刷屏?
因為創意人和設計師的方寸亂了,在diss和宣泄的同時,內心也開始陷入了深深的焦慮和恐懼。“到底什么樣的創意是好創意?”“什么樣的設計是好設計?”這事已經變得沒譜了。
盡管對設計的評價和感受是很主觀的事,但是,一直以來,大家心底里總還有一種默契,那就是所謂的“設計的金線”,這個金線就像馮唐在給韓寒的公開信中說的那樣:“文學的標準的確很難量化,但是文學的確有一條金線,一部作品達到了就是達到了,沒達到就是沒達到,對于門外人,若隱若現,對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洞若觀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雖然知道這條金線的人不多,但是還沒死絕。”
對于設計來說,那條金線應該是符合美學的基本原理,符合大眾的審美趣味,在形式上是新穎的,歡迎腦洞大開,可以出乎意料之外,同時也應該合乎情理之中。上面這兩個logo,一個是本土頂級廣告公司華與華的作品,一個是國際級大師的作品,但是,如果沒有兩大流量網紅的公開發布,如果作者不署名,估計很多人會認為是設計新手的涂鴉之作,看都懶得看一眼。
對于乙方來說,如果“客戶買單的創意(設計)才是好創意(設計)”,那么,這到底是降低了設計門檻,還是加大了設計難度?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反正,我身邊的人都開始亂了。
本文由“一品內容官”微信公眾號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Meta新社交平臺Threads上線五天用戶增至一億
中新社舊金山7月11日電 Meta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當地時間10日宣布,該公司推出僅5天的社交平臺Threads注冊人數增至1億。
扎克伯格在Threads上宣布了這一消息,此前他曾多次更新該平臺的用戶數量。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Threads的用戶數量增速打破了ChatGPT創下的紀錄,后者的用戶數量突破1億用了兩個月。
Threads與推特的功能較為相似,用戶可在平臺上分享簡短的文字,并發布照片及視頻。據《華爾街日報》近期報道,至少有兩家第三方機構表示,Threads上線之后,推特的流量一直在下降,這表明用戶可能會放棄推特而轉向Threads。
自埃隆·馬斯克去年收購推特并解雇數千名員工以來,該平臺屢屢遭遇技術故障。馬斯克還在推特平臺推行收費服務,并解禁了一些右翼人士的賬戶。最近,推特開始限制用戶可瀏覽的推文數量,其中付費用戶能看到的推文數量遠遠高于普通用戶。在一系列問題的影響下,許多推特用戶表示希望找到替代方案。
此外,Meta旗下的社交平臺“照片墻”用戶可直接登錄Threads,大大加快了后者用戶數量的增長速度。據報道,“照片墻”擁有數倍于推特的活躍用戶數量。
Threads上線幾天后,推特的律師在給Meta的信中指責后者系統、故意、非法地使用推特的商業機密和其它知識產權,并挖走其員工以打造Threads平臺。Meta發言人表示,Threads工程團隊中沒有推特前員工。
10日,微軟、蘋果、亞馬遜和字母表等大型科技公司股價均出現下跌,而Meta股價收漲超1%,逼近最近一年半以來的高位。(完)
來源: 中國新聞網
廣州成立公共交通集團 總資產達153億元
近日,廣州市公共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公交集團”)在廣州揭牌成立,囊括12家企事業單位、總資產達153億元,經營版圖涵蓋公共汽電車客運、輪渡客運、出租車客運、公路旅客運輸等范疇。
公交集團是廣州市政府全資大型國有企業,由12家市屬國有公共交通企事業單位組建,擁有“友愛在車廂”“如約”“白云放心車”“天字碼頭珠江游”“羊城一卡通”等市民、游客熟知的優質品牌,擁有公交車輛13253輛、公交線路1213條,水上公交船舶48艘、碼頭34座、水巴航線14條,出租汽車9353輛等。
公交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陳萬雄表示,公交集團將秉承公交優先原則,立足乘客服務,改善出行體驗,著力提升公交電動化、移動支付、如約平臺、定制客運等服務水平,打造品牌名片式公交服務。還將積極開展“交通+旅游”創新試點項目、發展醫藥物流、冷鏈物流等現代物流項目以及公交綜合體試點建設等,建設便捷、安全、共享、綠色的公交服務系統。
揭牌活動上,廣州公交集團還與白云機場股份公司、廣汽集團、地鐵集團等企業簽訂合作協議,并與騰訊公司、廣州移動、中科院廣州軟件所等聯合啟動成立廣州智慧公共交通聯合創新研究院。
成為圖書館員后,她擺脫了憂郁癥
艾莉·摩根,一個原本傷痕累累的抑郁癥患者。而這改變發生于她決定成為圖書館員的那一刻。
這是一家蘇格蘭的社區圖書館,不過它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館藏豐富,人間天堂。作家博爾赫斯那句廣為流傳的話“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用在這里大概也有一些違和,因為據艾莉·摩根第一天上班的觀察,這家圖書館似乎沒有多少人光顧,書籍沾有灰塵,整個空間一片死氣沉沉的樣子。如果說一個人對圖書館有期待,那么到了這里無疑會失望。
《書店》(The Bookshop,2017)劇照。
然而,也就是在這家圖書館,艾莉·摩根和圖書館完成了一種雙向拯救。在這里,她遇到了各色讀者,有超乎她理解范圍的貧窮人,有天真爛漫的孩子,他們終究找回了生活的意義。
艾莉·摩根將其經歷和感受記錄了下來。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新書《圖書館療愈手記》,內容為作者初到科繆爾(作者虛構的城區名)圖書館。摘編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起。注釋見原書。
《圖書館療愈手記》,[英]艾莉·摩根 著,魏華榮 譯,九州出版社·后浪,2023年1月。
我活著,就是一種錯吧
參加圖書館員面試的那天,我打定主意不要去死。就是說,我興許應該再多活兩天,如果我能忍住不死。第二天,我收到通知說我面試失敗了,沒法去圖書館工作了,我就改主意了。之前幾個月,我的想法在死與不死之間反復橫跳,我都數不清變了多少次。但這次感覺要來真的了,很像是個正經計劃。好計劃向來令我心動。我已經至少十二小時沒有反悔,這就更讓我覺得穩了。一了百了,到此為止吧。
不是我一心求死。事實上,死亡對我一點吸引力也沒有。只不過我提醒自己,這完美地合乎邏輯——去死是我道德上的義務。我也不是沒考慮過不死而只是出走,想個辦法斬斷自己與外界人事不斷減少的聯系。我如果能從這一切中赤條條離去,我絕對會這么做。說不定去法國呢,法國挺好。
問題就在于,事情從來不會那么簡單。我走了,別人就會擔心,而且我怎么個走法?我又不能開車。我得去乘坐公共交通,這可以被追蹤到,就像我不管用什么支付方式,也都會留下蹤跡一樣,更何況我銀行賬戶的情況也在走下坡路。如果我缺席下一次社區心理健康小組的會面,就要接受相關人士的盤問,至少逃不過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指責我浪費了國民保健署的寶貴資源。
《海倫》(Helen,2009)劇照。
細想來,實在是沒有別的出路了。左不過就是我死,接著寥寥幾人哀悼——我丈夫,我爸媽,我弟弟,最多再加上幾個遠房親戚——然后沒了我,生活繼續。“繼續”才是重點。
我很清楚我的腦子里住著一對小妖精,實際上我常常認為自己就是第三只身量大點兒的妖精,如果你想的話,你可以叫我“巨精”。這一對小妖精里的老大是我的老熟人了,我們差不多可以算是自幼相識,他被喚作“抑郁”。老二則更狡猾,藏得更深,最近我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是“創傷”,這家伙從我十二歲左右就在我的腦殼里搭便車,如果腦殼君跟我一個年紀的話。
我仍然很難將自己的內心想法和這兩個小妖精的聲音分清楚,后來才發現給我這最新的自裁大計煽風點火的一直是這一對鬼氣森森的拍檔。我這個人講邏輯、憤世嫉俗、有文化,我一直以此為豪,這他倆絕對知道。因為他們對我了如指掌,在那段時間甚至比我自己還要了解自己。
最終妖精組“好心提醒”我,人活著要么給別人的生活增色,要么讓別人的生活失色,而不巧我就屬于失色組。
《憂郁癥》(Melancholia,2011)劇照。
就拿我可憐的丈夫來說吧,現在我情況太差到沒法工作,他就得在經濟和情緒上支持我(“你是太懶吧?”妖精組時不時在我腦子里這么來一句)。我爸媽呢,勤勤懇懇工作這么多年,把我養大,供我讀大學,而我現在學也退了,又沒工作,精神狀況還不穩定,他們一定失望透頂。當然他們從沒說出來,但光是靠邏輯就可以猜到了,不是嗎?
因此,道德上正確的做法是——甚至我有義務這么做——把自己從這些人的生活中剔除出去,這樣才能幫他們卸下我這個討人嫌的重擔。
我正要繼續計劃的第二階段,即“構思行動”的時候,電話響了。
圖書館的來電
電話是圖書館打來的。得了,也不會更糟糕吧。我可能落下了什么東西,或者不小心順走了不屬于我的某份文件。好尷尬啊。
“你好,請問是艾莉嗎?”
我邊點頭邊說“對”。直到現在,我在電話里認同什么的時候還是會跟著點頭。“……情況有變。我們最終還是決定錄用你了。”“啥?對……對不起,信號不太好。能勞煩您再說一遍嗎?”“沒問題。我們決定錄用你做圖書館員了。你下周可以入職嗎?”
就在那一刻,我決定了,計劃第二階段也許可以稍后再議。畢竟今天我實實在在是小有所成,盡管有些彎彎繞繞。我怎么著也可以至少等到下一次出丑(說不定我把圖書館燒了,或者把領帶卡進復印機然后勒死了自己)再邁向第二階段吧。
“啊,好的。好,我可以。”
《布萊克書店》(Black Books,2002)第二季劇照。
如果你也想成為圖書館員,那我恐怕得告訴你,要進圖書館工作,沒有什么“成功范式”。我們都是走了五花八門的路子入了這行,很多時候完全只是機緣巧合。
但是機緣其實比你想的要可靠得多。做圖書館員的都是特定的一類人,就憑你現在在讀我的故事,你屬于這類人的概率就大大提升了。
做這一行并不需要你瘋頭瘋腦,但的確需要你對你做的事情有一點小小的狂熱。如果你又有那么點熱愛著書,那就更好了。
我小時候很幸運。基本上我整個童年都能泡在一個巨大的(對兒時的我來說簡直是無邊無際的)本地圖書館里,它就坐落在我家鄉的中心。好多我珍藏的回憶就發生在那些高聳的書架之間。
我兒時的那家圖書館現在應該會被稱為“社區樞紐”,或者頂著什么同樣無聊又商業化的名頭,但我小時候就直白地叫它“大圖書館”。在我眼中,大圖書館就是魔法,我對此從未宣之于口但一直深信不疑。不是迪士尼電影中那些童話里的塑料魔法,而是古老的魔法——嚴肅的魔法,與格林童話更為相配,它也生長在各地水泥操場上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里。
大圖書館是一個結界:一邊是俗世,混雜著各種校服、乘法表、體育服、午餐盒;一邊是另一個世界,神秘莫測,野性十足。在這里,每部鴻篇巨著都有自己的獨特天地。你只要找到一個安靜的角落(幸運的是那時候到處都是),就可以變成海盜、巫師、馴龍高手、吸血鬼,過一會兒,你又可以變成調查犯罪的偵探,或是充滿生存智慧,游走在三教九流之間的刑偵心理專家,或者你就是個平平無奇的普通人,卻卷入了一場跨越幾個大洲甚至幾個世界的陰謀。
大圖書館也是一個迷宮。那一列列書架是我這個小書蟲拼盡力氣也無法探索遍的。當我年紀足夠大,從兒童區“畢業”的那一刻,整棟圖書館都在呼喚著我。
上班第一天
科繆爾圖書館,也就是我要去的那一家,就在本地的一個社區中心里。曾經有一段時間,圖書館占據了整棟建筑:四面八方全是書架,樓上是兒童館,還有就是空間——充裕的空間,可以舉辦各種活動,很像我鐘愛的兒時記憶里那種充滿魔法的布局。
如今,科繆爾圖書館真實解釋了什么叫“虎落平陽”。整個館被貶謫到了社區中心后面的角落里,縮成了一個長手套一般狹窄的房間,從這棟磚石建筑的中間延伸到最后面,寄生蟲似的茍延殘喘。只剩一扇窗戶是朝外的,實在照不進什么光,所以在營業時間段天花板吊著的鹵素燈就得一直開著,閃個不停。整體能見度沒怎么好轉,陰影倒是加深了。
《圖書館員》(The Librarians,2014)第一季劇照。
重新改造這棟建筑的時候,有些窗戶原來朝著外面街道,現在朝向中心里面了,但大家都懶得去拆,所以窗戶上面仍然裝著鍛鐵欄桿。我把頭擠進欄桿中間,瞇著眼看向烏漆墨黑的里面。
圖書館固執地空著。正當我把頭從欄桿中間拔出來的時候,傳來了橡膠鞋底摩擦瓷磚的聲響,吱吱地宣告我的領導來了,她叫海瑟,負責我今天的培訓。她遲到了。
鑰匙從她手里滑出來,啪地掉在地上。她裹在大得過分的墊絨雨衣里,手忙腳亂地抱著一堆文件夾和她的手機。她撿完鑰匙直起身才注意到我,低盤在脖頸后的散亂發髻脫出絲絲縷縷的頭發,纏在她臉周圍。
“你在這兒干嗎?”她尖銳地質問,用眉筆描黑的眉毛擰在一起,日后這個標志性皺眉將天天招呼我,“圖書館關著呢。”
《書店女孩》(Páginas de Menina,2008)劇照。
“我是艾莉,”我答道,“今天入職?你上周還面試了我。”她的表情只稍稍放松了一點點;她忙著將鑰匙朝圖書館大門的鎖孔里捅,失手了好幾次,都劃拉在門漆上。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她想要幫忙,正要開口問她需不需要我幫著拿一兩個文件夾,她就一股腦兒地把它們全塞到了我懷里。“哦,對。是,不好意思。你今天看著和上次不太一樣。好了,我們來得遲了點,但不礙事,我給你講講,你就能趕上進度了。”她說這一串話的時候上氣不接下氣。我估摸著她跑了有一段路。如果開門時間的標識沒寫錯,圖書館十分鐘之內就要開始營業了。
我們跌跌撞撞地跨進去,我都來不及看看周圍。第一道厚重的木門后面是第二道門,更小些,也更現代。周圍全是五花八門的扣鎖、掛鎖和開關,感覺我像是走進了守衛嚴密的監獄。這是一個早秋的清晨,室內仍是一片昏暗。我踮著腳走進去,發現海瑟已經設法靈巧地挪進了信息技術區,一路上拍開一大長串燈開關,然后快準狠地摁警報代碼。燈閃著,一盞接著一盞,亮了起來。
我面試的時候來過一次這里,所以也不算完全陌生。一進門,正前方就是接待處,接待處旁邊用塑料隔板和書架圍出了一塊信息技術區,與圖書館其他地方分隔開來。這樣一番布局,使得只有芝麻大的信息技術區能照到一點自然光,靠后的兒童區則榮登“漆黑榜首”。燈嗡嗡地接連亮起,圖書館剩下的區域也隨之展露真容。
“好了……鑰匙。”海瑟一直在自言自語。我有心想聽個明白,但只聽到一些碎碎念。她拉開抽屜,把東西扔進櫥柜,又摸索著解開她那件大雨衣的扣子。
我把她那沓文件夾放在員工電腦旁邊的桌上,然后跟在她身后,盡量隔開一段安全距離——不太容易,畢竟接待處很明顯本來就只能容下一個人的。海瑟趕著為開門做準備的時候,我找了個機會把自己的個人物品放進了員工室的儲物柜,從早晨的滿身寒意里回過神來。海瑟把一張紙塞進我手里,催著我去找支筆。
《圖書館員:尋找命運之矛的探險》(The Librarian: Quest for the Spear,2004)劇照。
“開門流程,”她講解著,“照著單子來,完成一項就打個鉤。我本來想再詳細講講的,但今天我們遲了所以來不及了。”
行吧,又說遲到的是“我們”。“反正很簡單的,”她一邊說道,一邊飛速在圖書館里走來走去,“你就開門,開燈,輸入警報代碼,就寫在你的流程表上,喏;再關門,打開百葉窗,打開員工電腦,再開公共電腦—啊,顯示器卡了不要緊,老有人拽掉電源開關—登入歸檔系統,再把掛鎖放進抽屜……”
我試圖插嘴問一句掛鎖哪來的,無奈她滔滔不絕。我試圖瀏覽流程表,無奈這種公司文件似乎每一步都寫滿行話,我開始有點跟不上了。
“哦,還有健康和安全!”她突然來了一句,“健康和安全永遠是第一位。我們馬上就會要接受審核。老天,我還要讓你簽一下所有的……哎也不重要。看這個。”
海瑟站在一個半高的壁柜邊。壁柜的門過于寒磣,只能算一個開口。她像獄卒般從一大串鑰匙里找出一把開了門。
“在這里面要時時注意,小心碰頭。現在就我進去,你還沒有接受密閉空間訓練。”
光是想到“密閉空間訓練”,一絲幽閉恐懼的焦慮就已經刺進了我心里。但我只是點點頭,然后跟上去。開口后面是我只能形容為建筑石墻中間夾著的爬行空間。
人在這里面都站不直。海瑟貓著腰進去,開始按照流程從爬行空間里的鐵制的小保險箱取現金。我探頭進去,同時努力說服自己,所有聽見的窸窸窣窣聲都是我的幻覺。
“看在老天爺的分上,蒙特里梭!”我莫名地想起這句話,然后努力想這句話是從哪兒來的,為什么這么熟悉,海瑟在一邊繼續忙她的。
總的來說,我們開門也就遲了兩三分鐘。我還在想那句話,海瑟已經大手一揮,重新打開了入口的大門。
死氣沉沉,破破爛爛
事實證明,圖書館助理培訓基本上就是由一堆清單構成的。事實上,這個崗位本身基本上就是圍著清單轉的。
我以前做過歸檔工作,所以對用來借還書的系統還算熟悉。我也沒用多久就學會了操作條形碼掃描器和收銀機。
但是!清單真是要了老命。
《圖書館員》(The Librarians,2017)第四季劇照。
我們要記錄客流量,海瑟跟我解釋。門口裝了激光傳感器,激光束每被打斷一次,就增加一個客流數,多多益善。各個圖書館的撥款配置(連帶職員配置和營業時間)就是基于客流量。如果有個張三,一天在門口來來回回好多次然后一本書也不借,那也無所謂。我們就算一本書都借不出去也沒關系,只要保證高客流量,就萬事大吉。
我想著怎么不安排個人在決定客流量的激光束前來回揮手。興許他們確實試過。
接下來講藏書。這家圖書館里,實體書占據了最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水平空間。藏書流動大部分局限在兒童區。大字號書總是被常客輪著借。犯罪小說表現還可以。別的呢……就坐在書架上積灰。
客流大部分是沖著信息技術區來的。整個區域被電腦塞得滿滿當當。這些才是能掙錢的。上網免費,只要你是圖書館會員。人們大多是來上網搜索工作的。打印十五便士一張—圖書館大部分收入的來源。
海瑟進一步介紹信息技術服務的時候,我漸漸地開始目光呆滯。這些電腦有些年頭了,上面運行的微軟版本舊到我已經好多年沒見過了。鍵盤黏兮兮的,用的顯示器還是長寬比4∶3的那種。區議會的標準免責聲明在登入之后會彈出來,整篇用的字體都是加粗加斜的ComicSans(漫畫書字體)。
絕望如果能通過某種方式具象化,應該就是區議會運營的信息技術服務。激光打印機一股墨粉臭味。海瑟正給我演示如何給它更換紙張及清除卡紙。“它只能黑白打印,你看……”
《圖書館員:尋找命運之矛的探險》(The Librarian: Quest for the Spear,2004)劇照。
我盡量憋住內心的失望,這種失望真有點出乎意料。也不是說我對圖書館有什么別的期待,只是這也太……安靜了。死氣沉沉,破破爛爛。
甚至那些書好像也很難過,裹在灰蒙蒙的通用塑料書皮里。它們應當按字母順序排,雖然大致上也沒什么差錯,但從它們被放在架子上的方式可以看得出擺放的人極其不走心。小說被推擠到幾乎不存在的犄角旮旯里,毫無章法地堆著,有上下顛倒的、塑封壓扁了的、破了封面的、頁腳翻卷的,亂成一團糟。“當然,你需要簽完書本上架流程的文件,然后是信息技術的文件,還有數字隱私的……”
一些瑣事
海瑟一本本翻著接待處辦公桌上的活頁夾。我慢慢意識到,她指望我看完簽完她帶來的所有東西。
“呃……為什么精裝書要分開放呀?”我終于抓住她講話中罕見的間隙,插上了一問。
“嗯?”“在言情區。精裝的和平裝的言情小說是分開放的。”“這樣比較合適。”我反咬嘴唇,想不通其中原因。讀者在意書的樣式嗎?就算是,這地方就丁點兒大,藏書也少得可憐,他們真能這么在乎?平裝書都放在塑料旋轉展示架上,順序全亂了,還皺巴巴的。
“我喜歡這樣安排。”海瑟說。她狐疑地打量我。我清清嗓子,指向桌上離我最近的表格,所幸標題正好是“SOP297-A:化學品儲存”(標準作業程序)。“所以……這份我也要簽咯?”
海瑟不再懷疑了,又重新開始照著臺本講。她點點頭:“是的,我們不久要迎來一次審核。你看,這些都要你來簽。”
“啊……那這份呢?”
《天使之城》(City of Angels,1998)劇照。
海瑟看我的眼神好像我又長出了一個頭。我暗暗罵自己,她是在開玩笑!很明顯她在開玩笑嘛!圖書館員怎么可能要去給游泳池去污。她帶來這沓文件夾,里面塞著區議會隨便發的流程文件,就是來跟我玩猜謎的,看我什么時候才會發覺。
“我估計泳池在員工室里對吧,哈哈。”我笑了,但她沒笑。她眉毛又擰起來了,嘴抿成一條直直的細線。“審核在即。”她重復道,“你需要接受培訓,然后在所有這些流程表上簽字。”我眨了眨眼。她沒在吹牛。她眼里一丁點打趣的火星都沒有。她是認真的。
我打開第一本活頁夾,拿出第一張流程表(“SOP100:閃電襲擊與急救”)開始讀。
第一周就是這樣:我來上班,資歷比我老的同事給我開門,然后就是讀表格,簽表格,讀清單,簽清單,寫清單,復印清單,打印郵件里的清單。
讀者讓圖書館“無以倫比”
比我預想的要快,沒過多久我就已經將圖書館開門關門的步驟爛熟于心。我也發現自己能熟練地在一片黑暗中找到警報器面板和那排控制燈光的開關,矮身鉆進爬行空間開保險箱時也可以不碰到頭,甚至能在面對會員的詢問時給出比較確定的回應。
秋意漸濃,夜越來越長,空氣中也有了寒意。開門前一小時內,常常見到有幾個窮苦人擠在科繆爾社區中心的門廳里。我逐漸認識了這些骨瘦如柴、窮困潦倒的人(有男有女,大多年紀輕輕,還總是客客氣氣的),知道他們原來是本地貧民區公寓大樓的租客,因交不上錢或因粗心大意的房東忘了續費而被切斷了供暖。
那時我目睹的貧困程度之深讓我大受震撼。我雖然出生在工薪階層,家里也的確有過比較困難的時候,但這些都不足以讓我有心理準備,去見證我們小圖書館和社區中心里一些訪客所經歷的日常現狀。
他們中就有一個叫亞倫的年輕人,曾是個嗑海洛因的癮君子,來圖書館從開門坐到關門,要么對著電腦,要么翻本小說。
《圖書館員:圣杯的詛咒》(The Librarian: The Curse of the Judas Chalice,2008)劇照。
有的日子里,亞倫是除了我之外圖書館里唯一的人,很快我們之間就有了點熟悉的感覺。我們會聊聊他找工作的情況(無用功,沒人愿意招有吸毒黑歷史的人)和他當天午飯想吃啥。(今天他決定不吃午飯,晚上就能吃上薯條了。有時候我見這個可憐孩子拿著條面包,就干吃白面包充饑。)
他說,窮很難熬,但其實無所事事才真的要命。無聊最是能把一個曾經的癮君子再次拉入毒癮的泥沼。他付不起購物或旅游的錢,所以他就來圖書館,試著讀讀書(他早早就因吸毒輟學所以認字基本都是自學),在電腦上打打游戲、找找工作、看看油管上沒完沒了的紀錄片。他的耳朵反反復復感染,聽力嚴重受損,所以就算他戴著耳機我也總能聽出他每天學的是什么。
亞倫很快與科繆爾圖書館的布置融為一體。我通常還沒進門就能先聞到他的氣味。他公寓里供熱水的鍋爐壞了,所以洗不成澡,他只能在身上澆點社區中心公廁里公用的廉價除臭劑了事。他沒有電話(反正住的地方也老是斷電),所以就依賴他的社工,別的人想聯系他只能打給圖書館。
《布萊克書店》(Black Books,2002)第二季劇照。
我偶爾會同意——雖然海瑟極其反對——亞倫和他的社工在樓上一個閑置的會議室見面。這個房間味道很大,甜膩膩濕津津的,本來不應該給公眾使用,但至少保證了私密性,能留給亞倫這孩子一絲體面。
在周末,本地小學的孩子會由父母或監護人陪同著一擁而入,來借和他們這學年歷史研究報告相關的書籍,主題不外乎維京人、羅馬、古希臘或二戰。
只有一個孩子是獨自前來。她七八歲的樣子,肉嘟嘟的,一看就快要拔個子了;一頭紅發亮亮的,總用破舊的淡藍色發圈扎起來。她盯著一排排五彩繽紛的童書—只是盯著,一只手虛點著臉頰上長了雀斑的小酒窩。
頭幾周我會問問她要不要幫忙,她聽了就搖搖頭,然后跑出去。
“挺逗一小姑娘,”亞倫評道,“我以前認識她爸。”同樣的情形重復了三周后,我決心一定要去結識一下這個紅頭發大眼睛的小姑娘。我能辨認出她眼神里的閃爍不定,我能感知到她躁動的小手下藏著的不安。我在那個小姑娘身上看見了自己,孤身一人,但再多踏一步,就能發現這個陌生的地方是避風的港灣。
她下一次來的時候,我正在前臺翻著羅爾德·達爾的《瑪蒂爾達》。她見了我,猶豫了一下,我就趁機搭話。
《書店》(The Bookshop,2017)劇照。
“這本我最喜歡了,”我說,把書拿起來,“你讀過嗎?”她搖搖頭。“哦,這本可好看了!講的是一個有超能力的小女孩!她用魔法打敗了欺負她的校長。”
小姑娘把手從臉上拿開放下。“什么樣的超能力呀?”
我把書遞給她:“她可以用念力移動外物。她超聰明的,比她認識的所有人都聰明機靈。”
小姑娘從我手上接過書,細細端詳。我第一次見她的感覺又回來了。她打量書的神情就擺明她想要成為讀者,甚至她可能已經會讀書了。她在圖書館踟躕不前,只是因為害怕陌生人。她默不作聲地拿著書去了兒童區,挑了一張塑料凳子坐下便開始讀。
亞倫“呵”了一聲,就又接著看他的紀錄片(關于二戰戰艦)。
原文作者/[英]艾莉·摩根
摘編/羅東
編輯/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付春愔
- 熱門文章
- 最近發表
- 隨機文章
- 標簽列表
-
- 最新留言
-